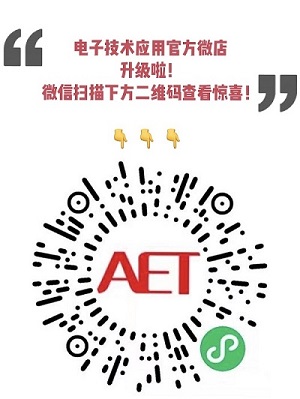自動駕駛賽道看上去坎坷不斷,但其實又蘊藏著蓬勃生機。最近,由于蔚來 NOP 領航輔助交通事故、特斯拉 Autopilot 遭美國 NHTSA 調查等事件,「自動駕駛」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
向前追溯,今年 4 月,全球自動駕駛領頭羊 Waymo 公司首席執行官 John Krafcik 官宣離職。5 月份,Waymo 首席財務官 Ger Dwyer 和汽車合作與企業發展主管 Adam Frost 相繼離職,也令不少人對自動駕駛前景感到唏噓。
實際上,與大部分新興技術的發展規律相似,自動駕駛仍處于螺旋式上升的初期階段。總體看,自動駕駛賽道目前共有四路玩家,分別是理想派、激進派、穩健派和掘金派。
1、理想派,以 Waymo 為代表,從 L4 自動駕駛入手,希望直接摘取高級別自動駕駛落地的果實;
2、激進派,以特斯拉、蔚來為代表,從輔助駕駛切入,通過不斷升級迭代的 OTA 向用戶開放更強的功能,并期望以量產車隊獲取的數據早日實現完全自動駕駛;
3、穩健派,以通用 Cruise 和長城毫末智行為代表,背靠規模量龐大的主機廠,較為注重自動駕駛及輔助駕駛功能的安全性,同時又在全速前進;
4、掘金派,以華為、大疆為代表,這些跨界玩家依托強大的研發實力,向主機廠提供智能汽車全棧解決方案,目的是在主營業務基礎上開辟出新的盈利點。
這四路玩家的發展模式雖然各有不同,但終局均是解放人類駕駛員,徹底變革汽車這一出行工具。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面臨質疑,但賽道上的玩家已經在接連發力。
今年以來,有著「中國版 Cruise」之稱的毫末智行披露了融資和產品落地消息。這家既有長城汽車的主機廠背景,又有著科技公司基因的自動駕駛公司,預計未來三年內搭載其輔助駕駛系統的乘用車輛將達到 100 萬輛。這一規模,意味著主機廠和科技公司「合體式」發展的穩健派正在走到聚光燈下。
如果只看當下,自動駕駛的發展的確充滿變數。但如果將視野拉長,又會發現自動駕駛技術其實一直在曲折向前,尤其是上面提到的車企主導型科技公司,正在逐步釋放出自身的能量。
四路玩家角逐,模式長短板日漸清晰
在自動駕駛賽道上耕耘幾年后,有四路玩家的發展模式和長短板已經逐漸清晰。
第一路玩家,主打「自上而下」的自動駕駛解決方案,從 L4 自動駕駛入手,目的是直接摘下果實。這一路玩家包括 Waymo、Uber、百度 Apollo 等。它們的優點是,背靠已經盈利的母公司,資金和人才供應十分充足。
不過,這一路玩家面臨的共同問題是,L4 自動駕駛技術挑戰巨大,仍需要后續大量資金和研發人才的投入,量產落地緩慢。從 Waymo 近期曝出的人事動蕩消息看,直接摘果更像是一種理想,但冰冷的現實卻是,自動駕駛在短期內很難自上而下進入量產落地階段。
原因在于,從高向低打,是要減少傳感器等硬件配置,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大量真實路測數據。
一位自動駕駛業內人士向汽車之心表示,特斯拉用了那么多年的毫米波雷達之所以能去掉,是因為積累了大量的路測數據。L4 的玩家從 2014 年左右開始布局,已經做了有五六年了,但是真實的道路數據并不多,投資方是否會愿意等它們五年還是一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路玩家如今其實已經出現分化。比如在打造 L4 自動駕駛之余,百度 Apollo 母公司百度已經與吉利合資成立了集度,選擇進場造車。這一舉措,未來對于百度 Apollo 的 L4 自動駕駛商業化落地也許會起到極大的推進作用。
第二路玩家,與第一類玩家剛好相反,這類公司追求的是從 L2 向 L4 逐級演進,以漸進式路線通往終點。這一路玩家還有一個特點是,雖然選擇了逐級演進,但是它們的推進節奏實際更快更激進。這類玩家主要為:特斯拉、蔚來、小鵬、理想等。
由于采取全棧式研發自動駕駛路線,第二路玩家領先于行業推出了高速道路下領航輔助駕駛功能,目前正在憑借視覺算法迭代和激光雷達傳感器的量產方案,嘗試開啟城市道路下的自動駕駛功能。
一方面,自動駕駛功能開發節奏遠超同行,另一方面,受限于 corner case 的天然約束,這讓第二路玩家收獲的掌聲和質疑從未間斷。
留給它們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一是能否一鼓作氣,逐級實現 L3、L4 自動駕駛功能的量產落地。
二是,除了特斯拉,蔚來、小鵬和理想的市場規模仍然相對較小,接下來能否持續放量,最終形成領導地位也有待觀察。
第三路玩家,同樣遵循從 L2 向 L4 逐級演進的漸進式路線。但與第二路玩家不同,這類玩家更加穩健。典型的玩家有,通用 Cruise、大眾 CARIAD 和長城毫末智行等。
這一路玩家的特點是,掌舵人由傳統車企出身,對于汽車行業的終局看得最為清晰,同時,公司的基因和組織架構又自帶科技公司屬性,能夠應對軟件迭代的迅速變化。它們的優劣勢會在下面進一步介紹,最大的風險是,能否持久地對自動駕駛進行投入。
最后的第四路玩家,屬于中途進入自動駕駛賽道的跨界者,目的是依托自身研發實力,成為汽車新時代的 Tier 2 甚至是 Tier 1,從汽車行業挖掘出豐厚利潤。主要玩家有:華為、大疆等。
其實,第四路玩家和第一路有部分相像,只不過,第四路玩家更注重商業變現。車企需要什么,他們就會去造什么。
第四路玩家的技術研發實力十分強大,問題在于能否讓主機廠放下戒備,展開全面深層次的合作。比如,此前上汽集團負責人就針對華為發表過「靈魂」言論。
總體來看,四路玩家各有長短板。Waymo 引領著自動駕駛技術的風向,同時也折射了 L4 落地的艱難。特斯拉、蔚來引領著自動駕駛量產的方向,同時也因為打了自動駕駛宣傳的擦邊球而輿論纏身。通用 Cruise、長城毫末智行更多地站在車企的維度,在自動駕駛激烈競爭中更加擅長長跑。華為、大疆則代表了跨界玩家的技術研發實力,還需要跟蹤它們自動駕駛賽道能夠走多遠。
站在當下,一方面頭部玩家需要重新審視自動駕駛技術方案的推進節奏和使用安全性提示。另一方面,接棒自動駕駛的任務,正在交到新的自動駕駛玩家手中。
沖刺型頭部玩家受到爭議時,長跑型玩家進入發力期
與 Waymo 等主研 L4 技術的自動駕駛公司曝出人事動蕩相似,特斯拉、蔚來和小鵬的自動駕駛功能其實也均遇到過質疑。
這背后反映的是,想要沖刺般迅速實現自動駕駛量產上車,其實有著很大的挑戰。舉個例子,特斯拉目前已經將 FSD 作為一大賣點。尤其是其最早研發的 Autopilot 系統,這一系統幾乎是時下行業對自動駕駛/輔助駕駛的代名詞。
特斯拉對于自動駕駛的持續投入,幫助其收獲了一大批對新興科技充滿興趣的消費人群。
國內的造車新勢力也借鑒了特斯拉的路徑。蔚來、小鵬和理想,這三家對自動駕駛的投入都相當可觀。截至目前,三家的自動駕駛團隊規模分別達到了 500 人、400 人、300 人,其中,蔚來和理想已經明確提出今年年底的目標是分別達到 800 人、600 人。
嚴格地講,特斯拉和造車新勢力三強相似,都屬于漸進式陣營的沖刺型選手。這類玩家會像特斯拉一樣持續推出自動駕駛相關功能,同時也承擔著產品功能完善性被質疑的風險。
另外,除了特斯拉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蔚來等三家尚處于發展初期,接下來能否持續擴大規模,繼續引領國內自動駕駛方向還有待后續地考量。
除了特斯拉和蔚來等,其實自主品牌發展自動駕駛還借鑒了國外的其他模式。比如,通用集團子公司 Cruise。2016 年 3 月,通用集團以 10 億美元收購了自動駕駛初創公司 Cruise。
目前,Cruise 已經獲得了授權,將可以在美國加州向乘客提供自動駕駛車輛打車服務,并將在 2022 年通用底特律的工廠進行自動駕駛車輛的批量生產。
Cruise 之所以能在量產方案上快速推進,離不開通用在背后的財務支持。而 Cruise 在自動駕駛領域的迅速成長,將來又會反哺給通用汽車的自動駕駛功能量產上車。
無論是特斯拉,還是通用 Cruise,均是由車企主導,由大規模的自動駕駛研發人才持續推進。馬斯克曾經表示,特斯拉就是一系列科技公司的結合體。特斯拉和通用 Cruise 的背后,均是基于車企自身對自動駕駛的發展需求,按照車企牽頭組建自動駕駛研發團隊模式進行技術攻關的。
與通用和 Cruise 采用類似協作模式的,是長城汽車與毫末智行。
毫末智行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任命長城汽車智能駕駛負責人張凱出任董事長,前百度自動駕駛高管顧維灝擔任 CEO。毫末智行的前身是長城汽車的智能駕駛部,核心團隊由長城汽車和來自自動駕駛 AI 領域的人才共同組成,這是典型的車企主導型科技公司管理架構。
一年半不到,也就是今年 2 月,毫末智行便宣布完成 Pre-A 輪數億元融資,由首鋼基金領投,美團、高瓴創投三家投資方跟投。
和 Cruise 主攻 L4 不同,毫末智行關于自動駕駛的布局主要有三個部分,也叫「風車戰略」,那就是乘用車輔助駕駛、低速無人車生態平臺和智能硬件。
其中,乘用車輔助駕駛是會更快量產上車的。
目前,毫末智行的業務范圍主要包括乘用車輔助駕駛系統和低速物流車自動駕駛方案,面向乘用車和低速末端物流市場形成了雙產品線戰略。
事實上,主機廠攻關自動駕駛研發,要么像特斯拉和蔚來一樣,選擇在內部孵化和組建自動駕駛團隊,要么就是通過收購的方式,像通用投資 Cruise、長城控股毫末智行一樣,通過車企與科技公司「合體」的方式進入自動駕駛賽道。
車企與科技公司合體,這種模式更加適合自動駕駛持久戰,因為它們背靠主機廠的新車市場規模,以及大量的資金和人才的投入,所以更適合自動駕駛的長跑。
一個佐證是,今年 6 月,成立尚且不到兩年的毫末智行,亮相了主打城市通勤場景的乘用車自動駕駛產品「小魔盒 1.5」、無人配送車「小魔駝」、無人車通用線控底盤「小魔盤」等 10 款產品,并且宣布已經商業落地了長城乘用車、美團無人配送車等多款車型。
根據毫末智行公布的數據,小魔盒行駛里程數突破 50 萬公里,搭載毫末智行輔助駕駛系統的長城高端車型「摩卡」已裝載 5000 臺,并在坦克 300 城市版也進行了量產。
此外,毫末智行的低速車產品「小魔駝」和「小魔盤」也已經啟動運營。
這樣的量產上車節奏已經非常快。要知道,這么短的時間周期,對于大部分 Tier 2 來說,可能也只不過拿下項目定點。技術方案不僅擁有迅速上車的機會,而且可以占領更大市場規模。
據了解,預計到 2022 年底,毫末智行的輔助駕駛系統將覆蓋長城汽車數十個乘用車型。張凱給出的數據是,「預計三年內,搭載毫末智行輔助駕駛系統的乘用車輛將達到 100 萬輛。」2020 年,長城汽車銷量達到 111.6 萬輛,預計到 2025 年銷量實現 400 萬輛。
只要毫末智行的技術方案產品力扎實,迅速地大規模量產會成為大概率事件。背靠主機廠,這就是以毫末智行為代表的車企主導型科技公司的“金鑰匙”。剩下的問題就是,由車企主導的科技公司,能夠進行多大規模的資金和人才投入。
站在長城的角度,對于自動駕駛幾乎已經是明牌。毫末智行的團隊目前已超過 500 人,設立了北京、保定和上海三個研發中心,預計到年底將達到 700 人以上。
長城預計在未來累計研發投入達 1000 億元,其中相當比例的經費分配給自動駕駛領域。按照長城制定的咖啡智駕「331 戰略」路線圖,其要在 2023 年要進入行業領導期,成為智能時代自動駕駛的領導者,實現「中國場景覆蓋最多的 L4 級自動駕駛」的目標。
毫末智行的「風車戰略」,或將與長城的自動駕駛發展協同共振。
所以,在自動駕駛終局到來之前,沖刺型選手 Waymo、特斯拉可能會不斷拋出重磅技術大招,而最擅長長跑的通用 Cruise、毫末智行等,也在進入發力階段,留給大家的主要問題就在于,主機廠對于自動駕駛是否有堅定的決心,以及能否進行持續地投入,成功接過領頭羊的自動駕駛量產大旗,繼續向前推進。
通往自動駕駛終局,事關榮譽乃至生死的戰斗
實現自動駕駛,是汽車行業玩家遭遇的一場事關榮譽乃至生死的戰斗。
對于 Waymo、華為這樣的外部競爭者而言,成功打入自動駕駛后,會再次向外界證明科技公司巨頭的強大實力,而一旦失敗,無非就是大量投入打了水漂,商業化探索最終折戟而歸,所以它更像是一場榮譽之戰。
至于主機廠,由于自動駕駛會對汽車出行工具進行本質上的變革,所以能否成功到達自動駕駛彼岸,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這也是為何賽道上的車企競爭日益激烈的原因。
市場上,我們已經看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毫末智行,百度控股的集度、理想汽車、華為智能汽車解決方案 BU 和上汽參投的 Momenta 等,均在擴大自動駕駛研發團隊規模,加快研發和量產節奏。
在競爭足夠激烈的行業背景下,上述四路玩家互相接力,整體上會推動自動駕駛早日量產落地。
那么,接下來四路玩家短期內會如何演進?根據已有部署和落地動作可以初步猜測,領頭羊 Waymo 特這類主攻 L4 的自動駕駛玩家,仍需要跨過融資關,能夠成功 IPO 進入二級市場進行融資,將有助于接下來的研發投入。
同時,眼下也不排除 L4 自動駕駛公司會「降維」與主機廠合作 L2-L3 自動駕駛方案,從而實現商業盈利。特斯拉和國內的造車新勢力,由于在智能汽車賽道上發力較早,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品牌認知。
雖然短期受到了市場質疑,但隨著視覺感知算法、激光雷達、大算力計算平臺等方案的不斷成熟,自動駕駛風景短期看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
通用 Cruise、長城毫末智行等玩家,由于是背靠主機廠,所以轉型動力更足,資金和人才保障更加確定,但其作為后來者的身份入局,策略、功能方案和行業聲量并不像特斯拉等新興公司那樣引人矚目。
另外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它們的發展也要視車企發展自動駕駛的決心而定。
一位業內人士此前向汽車之心表達過一種擔憂,「帶有國資背景的主機廠發展自動駕駛存在不確定性,比如,這一代管理層決定在自動駕駛方案中采用的激光雷達,很可能再下一代方案中又給拆掉了」。
也就是說,車企主導型科技公司的主要風險就在于,能否堅定的對自動駕駛進行持續投入。只要決心足夠大,便可以持續地向自動駕駛終局靠近。
總體來看,在漫長的自動駕駛道路上,有玩家會引領風向,也有玩家會替整個行業背鍋,當然也會有公司更加適合長跑。
與所有偉大的挑戰一樣,這個賽道上的玩家會漸漸發現,只有進場后不退場,保持定力和持續投入,才可能真正出現自動駕駛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