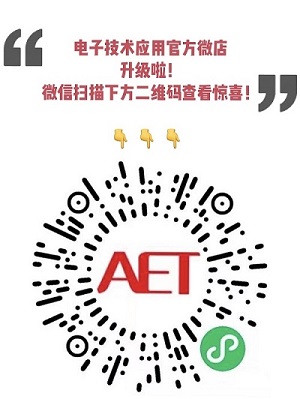常言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半導體行業亦是如此,技術和商業護城河建立后,剩下的不一定就是躺贏,可能是重重的“守江山難”。可能是技術快速的更迭帶來壓力,迫使半導體公司不停地升級甚至轉型,也可能是外力的擠壓,合作無方,獨立自主能力不得不加強。
中國的半導體行業發展數十年,我們在不斷地打下自己的江山,快速占領國際市場,但是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我們仍然面臨許多挑戰和困難,美國制裁、自身基礎薄弱、關鍵技術難以突破……
在中國半導體歷史發展的滾滾潮流中,逆流中知難而上的領軍人物顯得尤其珍貴,他們的存在,是未來的風向標,是中國半導體發展的底氣。
時代造英雄,在此前的文章《改變中國半導體的5個名字》中我們介紹了五位中國半導體的開拓者;英雄書寫時代,本篇文章將介紹為中國半導體的“保衛者”。
扁舟而上——江上舟
江上舟有很多名字,他是敢為天下先的“闖海人”,也是拒絕循規蹈矩的“官二代”,但最為人知曉的想必是:張汝京之后的中芯國際董事長。2011年病逝,在病床上能喚醒他的是“裝備樣機很成功”,他的一生,都在守著“中國芯”這座江山。
江上舟是一位中央蘇區老紅軍的后代,生于戰火紛飛的建國前夕,“文革”前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之后在瑞士留學八年。改革開放后的十幾年后,大陸地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解決11億人的就業和溫飽問題,招商引資以及引入國外技術是發展硬道理。都說官員是“放下身段”,是真心為民。江上舟就是其中一員,在高效布局了當時頗受非議的洋浦的基礎設施和洽談引入第一家大型外商之后,他被調到了上海經委工作,這也是他和芯片故事的開始。
如今的上海挑起中國高科技制造的大梁,江上舟居功甚偉。他首先認識到半導體芯片是國之重器,雖然趕超先進不是五年十年能實現的,哪怕面臨著政績壓力,江上舟還是決定踏出第一步。1998年,由江上舟策劃,馬啟元執筆,虞華年、楊雄哲等四人聯名撰寫的“建議”——《關于微電子產業發展建議》呈交給江澤民主席、朱镕基總理,里邊的思想是:一定要改變我國“微電子產業現狀甚為薄弱,不能帶動相關產業”的現狀。主要問題是產業規模小、技術水平低、經濟效益差、國家投資少、人才隊伍弱。
這封信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效果是明顯的。國家馬上行動起來召開內部微電子策劃會,此會被稱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里程碑”。之后相關政策出爐,江上舟和海外學子聯系、和國內大學教授合作,期盼著中國大陸半導體電子產業春天的到來。
他、張汝京、中芯國際
中國半導體事業更上一層樓跟張汝京創立中芯國際有著切不斷的聯系,我們知道江上舟臨危受命在張汝京之后接手了中芯國際,但不知道張汝京的回國其實和江上舟也是有著密切的聯系。江上舟提到:“當時,張汝京想要回國,要我們保密,我把當時國家鼓勵海外學子回國的內容用電話的方式告訴了張汝京,讓他了解會有新政策出臺,進一步鼓勵他下決心回來。”
后來,張汝京和江上舟會晤了。當時張汝京有意離開中國臺灣的原公司,馬來西亞對張汝京也是緊追不放,張汝京留到了香港大學。江上舟和馬啟元都說:一定要把他拉到大陸來,于是想方設法繞著彎子請香港的精英人士把此事促成。
2000年,張汝京入住上海張江。同年美國國務院出臺新政策,對華禁止開放設備。9月國家信息產業部原則上批準中芯國際項目,張汝京湊了10億美元。開工大典的前一天晚上門廊柱子仍未準備妥當,但張汝京說,等著吧,相信奇跡。這個奇跡,可能也是中國半導體的奇跡。
張汝京回憶建立中芯國際的種種時說過“如果沒有江上舟,我早走了”。而江上舟提到此事時提到,中芯國際的建成還是靠上海市委、上海政府的大力支持,任何個人都是辦不成的。作為大陸第一個國際水平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代工廠,中芯國際的建立是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里程碑,使中國有機會棲身于這個領域中的制造大國之林。
中芯國際之后經歷的低迷是大眾所熟知的。2009年張汝京官司敗訴黯然下臺,中芯國際元氣大傷,江上舟又迎來了新的挑戰。
第一輪官司敗訴,臺積電緊追不放,再次起訴,甚至“證據確鑿”。對于大陸的談判,臺積電“不見”“不談”,江上舟通過游說,對方勉強答應在香港和張汝京、江上舟會見。一味地退縮和示好是沒有好結果的,江上舟聲色俱厲的與對方說道“你們如果堅持這官司打下去,你們就要做好承擔這樣做所帶來的任何不良后果的準備!”“今天必須做決定!”窮途末路,江上舟敢說敢做讓對方終于妥協。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電子產業最大的官司,江上舟希望全球排名第一的臺積電和排名第四的中芯國際和解,哪怕內外交困,他處理的依舊漂亮。
2009年,江上舟臨危受命成為中芯國際新任董事長。他在中芯國際時間不長,但處于起承轉合的關鍵節點,分量很重,吃的苦非常多。前任董事王陽元推薦他做董事長,是從“中國芯”發展的大局出發做的決定。在處理臺積電官司時,如果沒有江上舟力挽狂瀾,迫使對方在法院最終宣判之前同意和解,把損失降到最低,經濟損失還要大,中芯國際會被拖累很久。代工廠的規模缺失會導致國內半導體的產業基礎越來越脆弱。
當時的江上舟已經患癌,在2011年去世的前一周,他還在病榻上參與董事會,“集成電路”能喚醒病床上混沌的他,“裝備樣機很成功”能讓他安穩睡下。他為“中國芯”耗盡了能量,他拼盡全力開拓和守護中國半導體的江山。
從“備胎”到主力——何庭波
中興事件后,就有很多人想到了華為,同為通信設備廠商,也都“跨界”做手機,華為會更抗壓嗎?會的,因為華為有海思。
海思一度被認為是華為旗下最“神秘”的部門,20多年來自主研制出一代又一代芯片,從“可有可無的備胎”到撐起半邊天,這給了華為在當下時代競爭很大的底氣。
1991年,華為成立了自己的ASIC設計中心,專門負責設計“專用集成電路”,當時的華為還是一個資金緊張一度瀕臨關門的公司。2013年華為海思推出了麒麟910,這是他們的第一款SoC,盡管這沒有完全得到市場的認可,但它依舊表著海思自主研發的手機芯片已經開始登堂入室。不到一年,新一代麒麟芯片推出,與華為的新款旗艦手機一起,逐漸得到市場的認可。之后,麒麟芯片快速迭代,手機不斷更新,銷售額和美譽度節節攀升。
2020年,美國制裁令要求,所有代工廠為海思芯片的生產于2020年9月15日結束。這讓海思不在神秘,從幕后正式走上臺前。
打下華為江山的任正非這樣說:沒有創新,要在高科技行業中生存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個領域,沒有喘息的機會,哪怕只落后一點點,就意味著逐漸死亡。這能看出,華為死磕麒麟芯片不是備胎的選擇,是深思熟慮的決定,這個決定的正確性,跟海思總裁何庭波脫不了干系。
何庭波,1969年出生于湖南,北京郵電大學碩士畢業。在選擇專業時,她就看到了中國芯片技術的落后,于是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決然選擇了半導體。九十年代的大學生很少見也很值錢,作為市場上的香餑餑,大四時已經有國內好幾家大型公司向何庭波拋出了橄欖枝,出乎意料的,她選擇了當時不起眼的公司——華為,這也是之后讓她有“芯片女王”稱號的職場。
1998年智能手機市場一片混亂,2G才在我國才興起沒多久,華為宣布要研發3G,主力就是何庭波。在這次任務中表現優異,之后她又被派去美國硅谷學習,何庭波認識到了中國和歐美國家芯片之間的鴻溝,這也使她明白不能再閉門造車了,只有引進國外先進人才才能打破國外的壟斷跨越這條鴻溝。在這關鍵時刻,任正非每年給何庭波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囑托她一定要研究出屬于我國自己的芯片。而當時的華為一年的研發費用總共只有10個億,可見何庭波肩上的任務。
但是當時華為還沒有被美國制裁,任正非也坦然告訴何庭波,研究自己的芯片是為了不時之需,不到萬不得已不會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意味著何庭波的定位是一個“備胎”,極有可能不會有轉正的那一天。對于一個人的職業生涯而言,把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的時間都壓在了前途渺茫甚至外界看來沒有意義的研究上,值得嗎?何庭波的答案是毫不猶豫的答應。
豪言壯志和埋頭苦干都抵不過現實殘酷,十年、二十年,華為海思的金錢和精力都沒有結出正果,何庭波的團隊依然沒有放棄。2010年,巴龍700的誕生打破了高通壟斷全球芯片的市場格局,從此海思扭虧為盈。
2014年,海思發布的麒麟910的28nm工藝是當時的頂尖水平。但是在2019年,美國對華為實施大規模制裁,華為“無芯可用”,美國人等著看華為笑話,期待看中國半導體行業翹楚轟然倒塌。但是海思讓她們失望了,何庭波說:滔天巨浪方顯英雄本色,艱難困苦鑄造諾亞方舟。
滔天巨浪依舊
前路是艱險的
Gartner發布的2021年的全球半導體研究報告顯示,由于美國貿易制裁,影響了中國在全球芯片市場的整體份額,華為海思已跌出全球25大半導體供應商的排名。海思的收入下降了81%,從2020年的82億美元降至2021年的15億美元,收入大減了67億美元,這是美國制裁該公司及其母公司華為的直接結果。
但是今年,何庭波領導的海思在華為內部的"戰略"地位進一步提升。華為不僅沒有放棄海思,且釋放了華為加碼芯片領域的積極信號。海思從2012實驗室下的二級部門獨立出來,升級成為華為的一級部門,與華為云計算、智能汽車解決方案BU、運營商BG、企業BG、終端BG、數字能源、ICT產品與解決方案并列同級。這意味著海思不再是備胎,而是華為如今的“主力”。
我們有理由相信,何庭波的幾十年的研究成果給美國制裁強有力的回應;我們同樣可以相信,何庭波的這支隊伍可以不斷研究、開發,為未來做準備;我們更是堅信,海思是在美國制裁的冰雪之下看見的一片新葉,它代表著華為乃至中國半導體未來的整個新春。
守著中國半導體江山的人還有很多,正如江上舟一再強調的那樣,盡管近幾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在迅猛發展,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在不斷縮小,但還要清醒的認知到,無論從產業規模或技術水準來說,我們仍處于起步階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國一定要爭氣,也一定會爭氣。